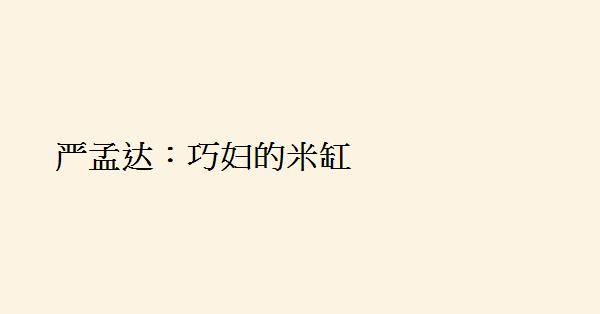
領導人的換班,總會帶來一些新氣象,這是國人所期待的。其實第四代已經為正式接班做了不小的鋪墊工作,如在生活費上漲的課題上。
11月8日舉行的第六屆彭博創新經濟論壇晚宴上,彭博社總編輯米思偉在專訪總理李顯龍時提出了一個小觀察,饒有趣味。當年,米思偉在李顯龍總理接棒不久后拜訪了建國總理李光耀,他詫異李光耀居然在內閣會議室上面的房間辦公。米思偉對此大驚小怪,我只能猜想他認為這有點不符合禮儀。
(作者是《聯合早報》特約評論員)
第二位總理吳作棟從李光耀手中接過治國重擔時,曾考慮過是否把總理公署遷出總統府。這是我國總理職位第一次換人,沒有前例可循,李光耀當時給他的一個意見是,如果他要保留政策的延續性,就不應該把總理公署搬出總統府,因為若這樣做,等于是向國人表示他將有所改變,或是要跟第一代政治領導人保持距離。因此,李光耀建議他接手自己的辦公室,并表示準備搬過去已看中的另一個總統府房間。但吳作棟出于對李光耀的尊敬,不敢勞駕李光耀,所以另外裝修一間房作為總理辦公室。
吳作棟在個人訪談錄《高難任務》里,把當年繼任時的這個小插曲說得生動有趣。他說,在西方的民主國家,領導人一不在位,就跟其他人一樣;但新加坡有自己的一套,前總理必須照顧一下繼任的新總理。
政府一邊調高消費稅,一邊多方補貼,看似矛盾,但是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」,巧婦的「米缸」不會自動填滿。米從哪里來?平民老百姓不能了解其中奧妙,以為生活費上漲本來就是政策造成的,也就因此不把政府的一切補助津貼當一回事。
所謂「不在其位,不謀其政」,似乎不適用于新加坡。前總理以資政的身份在內閣里繼續扮演獻策建言的謀士,又要避免把自己的看法強加在現任總理身上,對內閣是一門政治藝術。
行動黨武吉班讓區議員連榮華動議修正工人黨的動議字眼,強調「國會清楚生活費是全球關注的問題,呼吁政府繼續通過政策,減輕新加坡人和他們家庭面對的生活壓力……」,很顯然地是為了表示關心民間疾苦不是反對黨的專利。八名工人黨議員和兩名前進黨非選區議員反對無效,這項修正最后通過是必然結果,工人黨想必也為之氣結。
新加坡有別于其他民主國家的這一套,至今為止還是行之有效,今后能否保持下去,有待觀察。李總理最近在行動黨創黨70周年大會上宣布,他將在明年11月21日之前,讓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黃循財接任。到時李總理會扮演什麼角色,已是國人心頭上的一個疑問。米思偉的提問,顯示這也是國際媒體所感興趣的。
出自政府的口,沒有抽象的說詞,或是政治術語。李總理于彭博創新經濟論壇晚宴上說:「我國目前處于必須攜手做得更多和互相幫助的階段,政府必須參與其中,但必須努力避免所有問題都依靠政府來解決。」政府不養懶人的立場一以貫之,不會因新一代的上台而有所改變。
李總理的回應是,這是一個很微妙的事情,前任既要「照看」(overwatching),卻又不能「過度照管」(overbearing,《聯合早報》的報道中譯成「專橫」),前任必須「使用恰當、明智的話語,而不是束縛你的繼任者的風格」。李總理是過來人,知道「前任」的位置在哪里。
這場超過七小時的辯論,給明年底正式接班的第四代領袖提了個醒,「米缸問題」是他們領導力的一塊試金石,不能再靠前任指點江山。
前總理以資政的身份在內閣里繼續扮演獻策建言的謀士,又要避免把自己的看法強加在現任總理身上,對內閣是一門政治藝術。
工人黨領袖畢丹星近日在國會辯論中說,考慮到政府能在財政預算案之外撥出11億元的援助配套,以及當前的財政表現,工人黨質疑是否有必要在明年調高消費稅。幾日前,工人黨在國會提出「生活費危機」動議,促請政府檢討政策,減低新加坡人和家庭所面對的生活費壓力。朝野關心民瘼的出發點一致,卻各自表述。
政府能在預算案之外另外撥出巨資紓解民困,即表示國庫充實,國庫既然「錢飽飽」,為何還要繼續提高消費稅?反對黨的立論角度也許能引起一些人的共鳴,但也反映了政府必須生財有方,才能未雨綢繆,才能隨機應變的事實。
代交通部長兼財政部高級政務部長徐芳達反駁工人黨的論調時說:「反對黨必須坦誠,且保持一致的立場,不能在每次消費稅上調時就提出反對,卻又想動用上一輪消費稅上調所取得的收入。」
在新加坡,政府不說社會福利,只說「社會契約」,含義包羅生活各個層面。
在「新加坡攜手前進」的旗幟下,動員全民的參與,而不致流于一種由上而下的政治運動。
嚴禁無授權轉載,違者將面臨法律追究。



















